一、前言
自西元7世纪起至其后的一、二百年间,阿拉伯人初步建立起一个西起西班牙比利牛斯山脉,东至大唐西部边境与印度信德地区的横跨亚、非、欧的世界性帝国——阿拉伯帝国。这一帝国的文明达到很高的水准,其科学、技术及文化成就,即使在帝国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然保持领先地位,直至文艺复兴,世界科学中心才由那里转往欧洲。阿拉伯帝国的科学成就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不可磨灭的印记,它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篇章。
与其它文明不同的是,阿拉伯帝国的科学成就与伊斯兰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在伊斯兰进入阿拉伯土地之前的漫长岁月中,蒙昧的阿拉伯人以及帝国内其他一些后来皈依伊斯兰的民族完全笼罩在古埃及、印度、希腊、罗马与波斯文明的阴影之中。随着阿拉伯人版图与活动范围的扩张,许多民族如波斯人成为信奉由阿拉伯人率先传播的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由于践行伊斯兰所宣导的真主之下人人平等的思想,因此帝国的阿拉伯人及其他民族在科学文化上持宽容与兼收并蓄的态度,从而大大推动了那个时代科学的进步和发展。
二、科学成就
1、数学
任何十指健全的人都知道,从一数到十,最方便的记录方法是使用阿拉伯数字。这种奇妙的数字是聪明的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从印度人那儿吸收,并将之介绍到西方与东方的;同时,这些穆斯林向世界推广了数字“0”与十进位。具体地说,正是借助花拉子密(al’Khwarizmi,拉丁语名为Algorismus,西元780~850年)著名的《印度计算法》一书,这种对世界产生难以估量影响的奇妙数字才为世人了解并接受。因此,人们把这种数字称作阿拉伯数字。今天,阿拉伯数字已经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了。
阿拉伯数字无疑是方便而先进的数位体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爱好数学的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Sylvester II,西元945~1003年,任职:西元999~1003年)大约在西元1000年前后,曾经试图在基督教世界中推广使用这种数位体系,结果却收效甚微。
中学生进入中学学习的第一门数学课程是什么?答案是代数学。代数学是人类步入数学以及其它自然科学领域的基础。虽然代数学的萌芽久矣[代表人物:丢番图(Diophantus,西元200?~284年?)],但是它是在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手里正式成为数学的一门学科的。因此当后来的数学家们孜孜不倦地学习花拉子密的代数学著作时,没有人怀疑代数学是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创立的。
这位伟大的数学家在其著作中首次明确提出,代数学的数学问题都是由根(x)、平方(x2)和数(常数)三者组成,并且分六章叙述六种类型的一、二次方程的求解问题。花拉子密最具影响的代数学著作——《算术和代数论着》,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关于代数学的论着,此书的拉丁文译本直至文艺复兴时期还作为教科书在欧洲的大学中被广泛使用。
花拉子密对代数学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由他的名字——al’Khwarizmi的拉丁语译名——Algorismus,不仅派生出“Algorithm”或“Algorism”(“运算法则”或“十进位”),后来还演变出现在的对数一词——logarithm(简写为“log”);算术“arithmetic”一词的来源也与之类似。他在代数学中使用“还原、移项”一词的阿拉伯语音译“al-jabr”,传入欧洲后便演变为我们今天使用的“algebra”(代数)。
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史学家、《科学史导引》的作者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1884~1956年)对花拉子密的评价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迄今所有时代最崇高者之一”。他在赞扬花拉子密的代数学的意义的时候说:“在数学上,从希腊人的静态宇宙概念到伊斯兰的动态宇宙观,第一步是由现代代数学的奠基者——花拉子密迈出的。”希提(Phillip Hitti,1886~1978年)在《阿拉伯通史》中对花拉子密评价说:“他是伊斯兰教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对于数学思想影响之大,是中世纪时代任何著作家所不能及的。花拉子密不仅编辑了最古的天文表,而且编写了关于算术和代数学的最古老的书籍。”
阿布·卡米勒(Abu Kamil,西元850~930年)是花拉子密代数学的直接继承者之一,著名的《代数》一书就出自他的手笔,他本人也表明,他在代数学方面的工作是建立在花拉子密代数学基础之上的。阿布·卡米勒在代数学上的地位,可谓上承花拉子密,下启卡拉吉(al-Karaji,西元953~1029?年),而且还为义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奇(Fibonacci,1170~1250年)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外他还写了《测量与几何》与《计算技巧珍本》等诸多数学著作。《代数》其实包括三个部分的章节,即①二次方程的解法,②代数学在正五边形与十边形上的应用,及③丢番图等式与趣味数学问题;其中,第二部分章节,就是把埃及、巴比伦的实用数学与希腊的理论几何相结合,用几何学方法证明代数解法的合理性。《测量与几何》是一部指导大地测绘的实用性书籍,例如讲解如何测量各种不同图形的对角线、周长、面积,以及测量各种不同形状物体(六面体、棱柱体、棱锥体及圆锥体)的体积与表面积。《计算技巧珍本》则涵盖几何和代数两方面的内容,但其主要成就是关于四次方程的个别解法与如何处理无理系数的二次方程。除了上述留传下来的三部著作之外,西元10世纪的《科学书目》一书还列举了阿布·卡米勒另外一些著作,包括Book of Fortune、Book of the Key to Fortune、Book of the Adequate、Book on Omens、Book of the Kernel、Book of the Two Errors和Book on Augmentation and Diminution。
奥玛尔·海亚姆(Omar Khayyam,1048~1131年,兼诗人)是《代数问题的论证》(简称《代数学》)一书的作者,在数学尤其是代数学历史上堪称最杰出者之一。作者开创的用圆锥曲线解三次方程的方法,并依此将三次方程进行分类,可谓是对代数学发展的卓越贡献。奥玛尔·海亚姆的杰出还在于,他当时已经发现三次方程具有不止一个根,并且证明了另一个根的存在。他寄语后来人说到:“也许我们之后的人们会解决这个问题。”这一期望后来在16世纪由三位义大利人——费尔罗(del Ferro,1465~1526年)、塔塔利亚(Tartaglia,1499~1557年)与斐拉里(Ferrari,1522~1565年)变为现实,他们找到了解所有三个根的一般方法。另外,奥玛尔·海亚姆还进一步发展了二项式定理。
在希腊数学中,“数”的概念一般仅仅扩展到简单的加法和乘法运算,然而从算数运算到代数的飞跃,使人类第一次生长出在一切自然科学领空飞翔的翅膀……
阿拉伯人金迪(al’Kindi,西元801~873年)是那个时代的科学多面手,还是在算术学方面颇有造诣的数学家,并且写了许多这方面的著作,涉及范围包括印度(阿拉伯)数位、调和数、数位排列、相对值、比例、数位的处理与相消或相约,以及用有穷证明无穷等。在几何学方面,金迪擅长于平行理论的研究,他甚至给出一条(数学)引理以证明或否定某种可能性——即在同一平面上的数条直线,既非平行,也不相交。金迪还写了两本关于光几何学的书籍。根据1987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发现的苏莱曼时期的奥斯曼帝国的档案,金迪也是迄今已知的最早的(根据字母的使用频率)破译密码的专家,可谓密码分析学或密码破译学的鼻祖。金迪的手稿英译名为“On Deciphering Cryptographic Messages”(《密码资讯的破解》)。
塔比特(Thabit ibn Qurrah,西元826~901年,兼物理学家)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数学家,他在数学方面的地位主要在于,将数的概念扩展到实数,提出“积分”,建立了某些球面三角学及“解析几何”定理。他在西元850年左右写了一本书——《互满数的确定》,揭示了建立“互满数”的一般数学方法。
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对于数学的另一巨大贡献是三角学(三角函数),其学术思想可能主要来源于印度与希腊的三角学知识。三角学是随着一些探究宇宙奥秘的科学家在观测天体运行与研究天文历算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众所周知,研究天文演变的规律离不开三角学或数学知识,所以作为天文学家的最重要条件是,首先他必须是一位数学家。
阿拔斯王朝(西元750~1258年,中国史书称“黑衣大食”)的巴塔尼(al’Battani,欧洲人也称作Albatenius,西元850~929年)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天文学家与数学家。他完成了三角学的建立与系统化工作。在从事天文学研究的过程中,巴塔尼首先系统性地创建了三角学即三角函数这一数学分支的许多重要概念,如正弦、余弦、正切、余切。我们今天在中学学习的一些三角函数公式就是巴塔尼提出的;另外,关于球面三角形的余弦定理也是这位数学家对人类的贡献。而正割与余割的概念则是阿拉伯帝国的另一数学家兼天文学家瓦法(al‘Wafa,也称Albuzjani,西元940~998年)建立的,瓦法还指出正弦理论也可以运用在球面几何学上。
2、天文学
阿拉伯帝国的科学家们对天文学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在哈里发马蒙执政时期(西元813~833年),他们已经能够娴熟地运用诸如星盘、等高仪、象限仪、日晷仪、天球仪和地球仪之类的天文仪器从事天文学研究。
前文提及的巴塔尼(al’Battani,欧洲人也称作Albatenius,西元850~929年)是对欧洲影响最大的天文学家。他的《天文论着》(又名《星的科学》)颇具学术价值,后来的一大批天文学家诸如哥白尼(Copernicus,1473~1543年)、第谷(Tycho,1546~1601年)、开普勒(Kepler,1571~1630年)、伽利略(Galileo,1564~1642年)等人,无不研习巴塔尼的著作并受益非浅。他所创制的天文历表——《萨比天文》,一直是其后几个世纪欧洲天文学家的基本读物。
巴塔尼出生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哈兰(位于今土耳其东南部)的一个崇拜星辰的塞比教派家庭,这恐怕与其日后对天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以及学习制作天文仪器的技能不无影响;但是他本人则是虔诚的穆斯林。巴塔尼的工作主要是在阿拔斯王朝(西元750~1258年,中国史书称“黑衣大食”)著名的安条克(位于今土耳其境内)与拉卡(位于今叙利亚境内)天文台完成的。
这位伟大的天文学家的主要成就在于,他不仅编录了489颗天体,而且把一年的时间长度精确至365天5小时48分24秒,重新计算出(春秋二分点的)分点岁差为54.5‘,以及测定黄赤交角(赤道平面与黄道平面的交角)为23度35分(现在已知数值为23度26分)。它们比托勒密(Ptolemy,西元2世纪)的《天文学大成》的描述更为准确。巴塔尼提出地球在一条变动着的椭圆形轨道上运动(偏心率),发现太阳远地点的“进动”(即太阳距离地球最远点的位置是变化的,这是巴塔尼最著名的发现),以及认为日环食可能是一种日全食。他对于太阳运行的观测比哥白尼还要精确,并且在几个世纪之后还被上述欧洲的天文学家所采用。
巴塔尼的《天文论着》于1116年由义大利提沃利的普拉托(Plato,11~12世纪)译成拉丁语。
苏菲(al’Sufi,西元903~986年)所著《恒星图像》(或译作《恒星星座》),一书,是伊斯兰天文学观测的三大杰作之一。苏菲根据自己的实际观测,在书中确定了48颗恒星的位置、星等和颜色,并且绘制出精美的星图与列有恒星的黄经、黄纬及星等的星表。他还为许多天体进行了名称鉴定,提出许多天文术语,许多现在世界上通用的天体名称都来源于苏菲的命名,例如牵牛星、毕宿五、天津四等。苏菲的星图也是关于恒星亮度的珍贵的早期资料。西元964年,正是他最早记录下仙女星座。这位的天文学家对天文学界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苏菲星团”,国际天文学会还以用他的名字命名月球表面一处环形山来纪念他。
前文提及的瓦法(al‘Wafa,也称Albuzjani,西元940~998年)是巴格达天文学派最后一位著名人物。已知他曾测定过黄赤交角和分至点,并且是提出“月球出差”的第一位天文学家;此外他还为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编撰了简编本。
奥玛尔·海亚姆(Omar Khayyam,西元1048~1131年)在当时由突厥塞尔柱王朝管辖的伊斯法罕,参与并领导了天文历表的编撰与历法改革工作,制定的贾拉利历的精确程度已经十分接近格利高里历,根据这部历法测定一天的长度为365.24219858156天(后来由于政局的动荡历法改革工作被迫终止)。
比鲁尼(Biruni,西元973~1050年)堪称那个时代理论水准与实践能力俱佳的“天才”,天文学(与数学)是其深入涉足的领域。他在一部近1500页的著名的百科全书——《马苏迪之典》中,测定了太阳远地点的运动,并且首次指出其与岁差变化存在略微的差别。《马苏迪之典》是一部集天文、地理和民族学的通科著作。比鲁尼还设想地球是自转的。他在写给好友、同时代的著名医学家伊本·西那(ibn Sina,西方人称为阿维森纳Avicenna,西元980~1037年)的信中,甚至提出地球绕太阳运转的学说,并且认为行星的轨道是椭圆形而非圆形的。地球绕太阳运转的观点还表现在比鲁尼的一部天文学百科全书——《占星入门解答》之中。他说,如果认为地球是在围绕太阳运转的话,那么就不难解释其他星体的运动情况。另外,至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银河系,比鲁尼发现它是由“无数的各种星体组合而成”。
其实,比鲁尼是一位勤奋、多产、涉猎范围广博的科学家,他一生写作了涵盖20多门学科的大约146部著作(只有22部传世),其中多数是与数学及天文学有关的,例如《投影》。
在法提玛王朝(西元909~1171年,中国史书称“绿衣大食”)哈里发哈基姆(al’Hakim)统治时期(西元966~1020年),天文学家尤努斯(也译作尤尼,ibn Yunus,西元950?~1009年)在参考200多年以来天文观测资料的基础之上完成了《哈基姆星表》(也译作《哈基姆历数书》),并还用正交投影的方法解决了许多球面三角函数问题。尤努斯的杰出在于,他的计算细致而精准,例如,他注意到投向地平线的光线的折射所引起的误差,并且首次给出被观测物体的40分差角。他对月食的观测记录是极其可靠与可信的,其30次月食报告为近、现代天文学家,例如西蒙•;纽科姆(Simon Newcomb,1835~1909年),研究月球的长期加速度提供了珍贵的天文资料。
穆斯林的信仰要求礼拜的定时,而这与太阳与月亮或其它天体的运动是密切相关的。尤努斯就是一位可以给出精确时间的天文学家,而且他的天文历表可以在伊斯兰历、科普特历(一种古代埃及人使用的历法)、古叙利亚及波斯历之间进行转换或换算,以方便人们的使用。
1080年,西班牙穆斯林天文学查尔卡利(al’Zarqali,西方人称为Arzachel,11世纪)完成《托莱多星表》(也译作《托莱多天文表》),其中有天文仪器(尤其是阿拉伯人擅长的仪器——星盘)的结构介绍与使用方法。《托莱多星表》对托勒密体系进行了修正,以一个椭圆形的“均轮”代替“本轮”。另外,《天文表》也是查尔卡利的杰作。
在对于宇宙体系的认识上,穆斯林天文学家质疑托勒密的本轮学说,并试图建立一个真正的宇宙体系。
先后经历过阿拔斯王朝与蒙古人建立的伊尔汗国两个时代的天文学家(兼数学家)图西(al’Tusi,1201~1274年),不仅建立了月球的运动模型,而且还在1247年提出所谓的“图西力偶”定理(即线性运动可以由圆周匀速运动演化而成,反之亦然)。科学史学家乔治·萨里巴(George Saliba,1939~)在评价“图西力偶”定理时说:“如果仅靠欧几里得(Euclid,约西元前3世纪)的《几何原本》和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等古希腊的数学和天文著作中所提供的数学资讯,哥白尼天文学的数学大厦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构建这一大厦所需要的,实际上也是哥白尼本人所利用的,是两种新的数学原理。而这两种数学原理却都是在哥白尼以前大约300年间发现的,并为伊斯兰世界的天文学家们明确地用来改进希腊天文学。”文中所提到的数学原理之一,便是图西的“图西力偶”定理,它在16世纪初被哥白尼采用。
图西一生写作了关于天文、数学(几何与三角学)、物理、哲学、伦理学及逻辑学等学科的100多部著作,甚至还整理过伊本·西那的《医典》,但是其中最著名的是《伊尔汗天文表》(或译作《伊尔汗历数书》)。
位于今伊朗境内的、闻名遐迩的马拉盖天文台也是在图西倡议下建立于伊尔汗国初期,其天文仪器甚至在当时被带到中国的元大都。马拉盖天文台的遗迹至今尚存,成为人类文化遗产。
乔治·萨里巴在谈及阿拉伯帝国天文学与哥白尼天文学关系的时候说道:“当我们想到哥白尼天文学本身给我们带来的所谓‘哥白尼革命’这样的概念时……我们便不难想像到哥白尼的数学天文学与在他以前用阿拉伯语写作的天文学家们之间的交融了。或者换句话说,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阿拉伯天文学与哥白尼天文学之间的模糊边界会是这样有趣了。”
凯文·克里斯纳斯(Kevin Krisciunas)则对某些蓄意抹杀伊斯兰天文学成就的态度给予直率的批评。他在《世界天文学中心》一书第二章的开头即写到:“那种认为在托勒密之后,天文学研究陷入沉睡直到哥白尼时代才得以苏醒的看法,是一常见的错觉……那些认为阿拉伯人没有做出自己的贡献的人们,对于这一学科并未进行过调查研究。”他还进一步指出,中世纪的天文学家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用阿拉伯语书写科学著作的,即使是犹太人与基督徒也莫不如此。
事实上,阿拉伯帝国天文学在今天已经落下永久的烙印,甚至现在人们使用的很多与天文有关的词汇,诸如“azimuth”(地平经度、方位角)、“nadir”(天底)、“zenith”(天顶),等等,都是源自阿拉伯语。
可以肯定地讲,阿拉伯帝国的天文学家对于宇宙天体的认识,是人类天文学史上由托勒密到哥白尼之间最重要的衔接。
3、医药学
阿拉伯帝国在医学上取得了相当出色的成果。
拉齐(al’Razi,欧洲人称其为Rhazes,西元865~925?年)不但是一位杰出的化学家与哲学家,还是一位著名的医学家。他学识深邃而广泛,一生写作了200多部书,尤以医学(与化学)方面的著作影响巨大。拉齐曾先后担任雷伊(位于伊朗德黑兰附近)和巴格达医院院长,并从事学术著述,被誉为“阿拉伯的盖伦”、“穆斯林医学之父”。
拉齐在医学上广泛吸收希腊、印度、波斯、阿拉伯(甚至中国)的医学成果,并且创立了新的医疗体系与方法。他尤其在外科学(例如疝气、肾与膀胱结石、痔疮、关节疾病等)、儿科学(例如小儿痢疾)、传染病及疑难杂症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与理论知识。他是外科串线法、丝线止血和内科精神治疗法的发明者,也是首创外科缝合的肠线及用酒精“消毒”的医学家,还是世界上早期准确描述并鉴别天花与麻疹者(中国人认为中国的葛洪是最早描述天花症状的,在拉齐之前也有一位阿拉伯帝国的学者介绍过天花与麻疹,但拉齐的论述更为后人所了解),并且将它们归入儿科疾病范畴。拉齐注意到一种疾病出现的面部浮肿和卡他症状(如打喷嚏、流清涕),与玫瑰花生长及开放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他第一个指出所谓的花粉热就是缘于这种玫瑰花的“芳香”。
拉齐的代表作《曼苏尔医书》是医学史上的经典著作。他于西元903年把《曼苏尔医书》捐献给萨曼尼德的王子兼雷伊地区长官曼苏尔。《医学集成》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医学著作,作者花费15年的时间完成此书。《医学集成》主要讲述的是疾病、疾病进展与治疗效果。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保存有一部《医学集成》的阿拉伯语手抄本,它是在1094年由一位佚名抄写人抄写的,也是该馆最古老的医学藏书。
《曼苏尔医书》和《医学集成》分别于1187年与1279年在西班牙深受穆斯林文化影响的历史名城托莱多与法国的安茹被译成拉丁语而在欧洲广泛传播,并且随即取代了盖伦(Galen,西元130?~200?年)的医书;它们在文艺复兴时期又被多次翻印,并且由当时著名医学家加以注解。
此外他还着有《医学入门》、《医学止境》、《精神病学》、《天花与麻疹》、《药物学》、《盖伦医学书的疑点和矛盾》等。
拉齐确信,他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一定会被比他卓越的思想超越。在他看来,那些有志于科学研究的人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因为这是科学发展的规律。
伊本·西那(ibn Sina,西方人称为阿维森纳Avicenna,西元980~1037年)西元980年出生于中亚的历史名城布哈拉附近,是代表阿拉伯帝国医学最高境界的里程碑。他与希腊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西元前460?~370?年)、盖伦并称医学史上的三位鼻祖,被尊为“医者之尊”(“Doctor of Doctors”)。伊本·西那学识渊博,除了医学之外,他在其它方面也颇有造诣。
伊本·西那的医学成就主要体现于一部极其著名的百万字医学百科全书——《医典》。他在《医典》的开篇中说:“医学是这样一门科学,它告诉人们关于机体的健康状况,从而使人们在拥有健康的时候珍惜健康,并且帮助人们在失去健康的时候恢复健康。”《医典》一书全面而系统,全书包括5部分,分别讲述医学总论、药物学、人体疾病各论及全身性疾病等内容。
感染性疾病曾经一直是人类疾病的第一位死亡原因,今天人们已经认识到,这类疾病是由病原体例如致病性细菌、真菌与病毒等引起的。伊本·西那提出人本身以外的因素在引发疾病方面的作用,首先发现了“原体”可以是产生疾病的原因,指出肺结核就属于此类疾病,天花和麻疹也是由肉眼看不到的“原体”所致,而且还强调了“消毒”的重要性。他发现水与土壤可以是传播致病物质的媒介。伊本·西那不但认识到钩虫病是由肠道寄生虫引起的,并能够做出准确的诊断。
他主张外科医生应该在早期阶段治疗恶性肿瘤,以确保对所有病变组织加以切除。伊本·西那在著作里强调膳食营养的重要意义,提出气候和环境与疾病有关的观点。他研究过心脏瓣膜,发现主动脉有三个瓣膜,瓣膜的张开与关闭配合心脏的收缩与舒张,从而维持血液的流出与流入。伊本·西那描述和记录了有关心脏病药物的提炼及皮肤病、性病、神经病(例如脑膜炎)与精神疾病等病症。他还能够将纵膈炎与胸膜炎相鉴别。他也介绍了用烧灼治疯狗咬伤、针刺放血与竹筒灌肠以及音乐等疗法。
伊本·西那主张,在正式推广使用一种新药之前,首先应该进行动物与人体实验,从而保证药物的安全性。
《医典》从12世纪被译成拉丁文起直至17世纪的数百年间,始终被欧洲的医学院校用作医学教科书,仅在15世纪的最后30年内,这部著作就被用拉丁文出版过15个版次。它对西方医学的影响胜过任何一部医学著作。著名医学教育家奥斯勒(William Osler,1849~1919年)博士对《医典》的评价是“被当作医学圣经的时间比其它任何著作都要长”。《医典》是现代医学产生的重要基础之一。
其实,伊本·西那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他一生大约写了450部著作,它们不仅是关于医学的,还有专门论述哲学、心理学、地质学、数学、天文学、逻辑学与音乐等学科的,其中传世的有240部左右(关于哲学与医学的分别为150部与40部)。例如影响力仅次于《医典》的《治疗论》一书,本身就是一部百科全书。
出于对两位医学先驱的尊敬,拉齐与伊本·西那的画像今天仍然悬挂在巴黎大学医学院的画廊上。
西元10世纪的扎哈拉维(Abul Qasim al’Zahrawi,欧洲人称之为Abuicasis或Albucasis,阿尔布凯西斯,西元936~1013年)是出生在穆斯林治理下的西班牙的著名医学家,享有“外科学之父”的赞誉,其祖先来源于阿拉伯半岛的安萨尔部落。
扎哈拉维的《医学手册》是一部集其数十年医学知识与经验的著作,包括30篇的内容,涵盖大量临床问题,适用于执业医生与医学生。这部著作附有历史上最早的外科器械插图与文字说明,而且数量相当丰富(200幅左右)。这些精致的插图(与文字说明)使其极具学术价值。他还把外科治疗划分成几个部分,例如烧灼术、手术切除、放血疗法与接骨术。12世纪,《医学手册》的外科部分(第30篇)在托莱多被来自义大利克雷默那的翻译家杰拉德(Gerard,1114~1187年)翻译成拉丁语,并且在1497~1544年之间至少再版10次之多。从12~15或16世纪,几乎欧洲所有的医学家编撰的外科教科书无不参考或引用扎哈拉维原书的译本,例如Roger、Guglielmo Salicefte、Lanfranchi、Henri de Mondeville、Mondinus、Bruno、Guy de Chaulliac、Valescus、Nicholas及Leonardo da Bertapagatie等人。
扎哈拉维不仅改进了一些器械,还发明了许多外科器械,例如一种引流腹腔积液的斜面套管,插入尿道治疗尿路结石的探头,以及一种用于切开脓肿的隐蔽式手术刀。他还发明、引进了镊子、(羊)肠线以及今天妇产科医生使用的窥阴器与扩阴器等。
在《医学手册》的第一与第二篇里,扎哈拉维归类了325种疾病,讨论了它们的症状与治疗,并且在第145页上首次描述了一种由“健康”母亲传递给儿子的出血性疾病,也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血友病。这部分篇幅后来亦有拉丁文译本出现,名为“Liber Thoricae”。
在妇产科方面,扎哈拉维的著作包括指导训练助产士如何处理异常分娩,取出死胎与去除胎盘,以及剖腹产的实施方法等。
扎哈拉维对于后来的医学尤其是外科学具有很大的影响,人们也并没有忘记这位生活在1000年前医学家。现在,在扎哈拉维的家乡西班牙科尔多瓦,有一条叫做“Calle Albucasis”的街道,就是以他的拉丁化名字Albucasis命名的,意思是“阿尔布凯西斯(扎哈拉维)大街”;西班牙旅游局在这条街道的6号建筑物门前安放了一块铜匾,上书“阿布·凯西姆旧居”(“阿布·凯西姆”也是扎哈拉维的名字,取自其全名)。按扎哈拉维的设计而复原的外科器械,曾经在西班牙、突尼斯和巴基斯坦等地的博物馆中庄重地陈列展示,以表达人们对他的尊敬。
另一位出生在西班牙的医学家伊本·拉希德[ibn Rushd,拉丁名阿威罗伊(Averroes),1126~1198年]是研究组织学的先驱,他还发现患过天花的人以后不会沾染天花,他对血管与运动保健也颇有研究,西班牙与北非的摩洛哥都曾留下他工作的足迹。他的《医学原理》在当时是一部很全面的医学入门书籍。
除了医学之外,哲学与天文学也是伊本·拉希德研究的物件,尤其是在哲学方面,他的“阿威罗伊哲学”(Averroism)对西方学术界的影响力甚至大大胜过其在伊斯兰世界所享有的威望。
阿拉伯帝国的医学非常注重眼科疾病,医生们好像大多都对这方面的病症显示出浓厚的兴趣,而且具有很高的诊断与治疗眼科疾病的技艺。几乎所有的医学著作都有专门的篇章论述眼科疾病,但是最全面的关于眼科疾病的论述是以专着的形式讲述的。
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Hunayn ibn Ishaq,西元809~873年,欧洲人称之为Joannitius,兼翻译家与数学家,基督徒)写了多部眼科学专着,诸如《眼科问题》、《眼睛的结构》、《五彩斑斓》、《眼科疾病》、《眼病治疗》、《眼科疾病的手术疗法》……其中以《眼科十论》影响最大。
卡哈尔(Kahhal,西元940~ 1010年,可能是基督徒)则在其眼科学专着《眼科医师手册》里介绍了多达130种眼科疾病。
白内障是一种常见的眼科疾病,其病变部位在眼球的晶状体,未治者的结局常常是致盲。当时,聪明的医生已经知道它的治疗方法。与卡哈尔同时代的毛斯里(Mawsili),是白内障针吸术的发明者,这种技术即通过一种金属空心针经过巩膜吸除白内障病变。200多年后,即大约于1230年,有一位历史学家兼眼科医生在大马士革的一家医院里亲眼目睹过使用上述器械去除白内障的手术的过程。然而,14世纪埃及著名的眼科医生萨达卡(Sadaqah)对这种疗法的真实性表示质疑。
沙眼是又一眼科常见疾病,常引起倒睫、睑内翻及角膜血管翳,严重者也可致盲。当时的医生对于此症已有深刻的认识,他们不但对角膜血管翳给予清晰的描述,而且尤其擅长于手术切除这种长在角膜上的血管组织,但是这种手术的真实性似乎令人疑惑。他们在手术中使用一系列自己发明的手术器械,例如开眼器、拉钩、细小的手术刀和拨针。他们还能够采用类似的手术器械治疗翼状胬肉。
以当时的医学水准来看,上述手术是非常精细与复杂的,而且患者往往要忍受相当程度的疼痛,故帝国的医生可能并非常规进行这种手术。
在12~14世纪,在阿拉伯帝国范围内出现了许多眼科学著作,例如《眼科指南》与《眼科疾病治疗的思考》等,后者分17章讲述了眼的解剖、生理,以及124种眼科疾病的病因、症状和治疗,其中不乏在作者之前从未描述过的内容。它们在当时以及其后几百年间都是从医者学习眼科疾病的权威著作。
虽然眼科疾病早先一般是在外科疾病中讨论的,但是阿拉伯帝国的医生已经开始把眼科疾病从一般医学中独立出来,这就是现代眼科学学科的雏形。例如13世纪叙利亚医学家库弗(Quff,西元1233~1286年)在其编写的外科专用手册里,故意不收入任何眼科疾病,因为在他看来,眼部疾病应该属于专科医生的诊治范畴。
哈森(al’Haitham或al’Haytham,西元965~1040年,欧洲人称为Alhazen)不仅是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与数学家,他在研究光学原理的同时,也对人类眼科学或眼科生理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研究丰富了人们对于眼球的生理解剖和视觉原理的认识。今天眼科医生使用的“视网膜”、“角膜”、“玻璃体”及“前房液”等专业术语大多与哈森有关。
穆斯林是研究精神疾病的开拓者,而且在这一领域发挥了早期的作用。事实上这归功于拉齐的直接贡献,是他在巴格达为精神疾病患者建立了特别的病房。正如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医学教授赛义德(Ibrahim B. Syed)所言,穆斯林为“精神病学带来一种冷静的全新的意识”。因为穆斯林医学家根本不会相信在欧洲基督教世界盛行的精神疾病的“鬼魂学说”(鬼魂附体),所以他们能够对此类疾病进行冷静的临床观察。
13世纪大马士革的医学家纳菲(或称伊本·那非斯,ibn al’Nafis,1213~1288年)对盖仑的血液回圈学说进行了积极的批判。盖仑认为血液的流程是右心室→左心室,而纳菲发现心脏左右心室之间的隔膜很厚,而且隔膜上面没有像盖伦所设想的那种孔道,血液不可能从右心室直接流至左心室。为了纠正盖仑的谬误,纳菲提出一种血液小回圈(肺循环)理论,即血液在此的流程是右心室→肺动脉→肺(交换空气)→肺静脉→左心(房)室。这种血液小回圈理论比后来的塞尔维特(Servetus,1511~1553年,因蔑视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学说被宗教裁判所裁决处死)的发现要早300多年。遗憾的是他的学说并未在当时引起人们的重视,被淹没了700多年直至20世纪才重新被后人在布满尘埃的档案中发现。另外,1547年,安德里亚·阿尔帕戈(Andrea Alpago)曾经将伊本·纳菲的一些书稿翻译成拉丁语,因此欧洲人完全有条件了解伊本·纳菲的重要工作(甚至包括直接阅读阿拉伯语书稿),而就在这前后欧洲的医学家便获得了与伊本·纳菲相同的“发现”。难道这只是巧合?以下是纳菲手稿的英译。
“the blood from the right chamber of the heart must arrive at the left chamber, but there is no direct pathway between them. The thick septum of the heart is not perforated and does not have visible pores as some people thought or invisible pores as Galen thought. The blood from the right chamber must flow through the vena arteriosa (pulmonary artery) to the lungs, spread through its substance, be mingled with air, pass through the arteria venosa (Pulmonary vein) to reach the left chamber of the heart……the nourishment of the heart is from the blood that goes through the vessels that permeate the body of the heart……”
伊本·纳菲不仅正确揭示了肺的解剖结构,而且还是第一位记录心脏冠状动脉血液回圈的医学家。他写到“……心脏的营养物质来自沿这些血管运行的血液,而这些血管是分布于心脏的……”
除了前述的一些医学专论之外,阿拉伯帝国的一些医学家还写作了很多关于特殊疾病及相关药物的著作。例如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的儿子,易司哈格·伊本·侯奈因(Ishaq ibn Hunayn,西元?~910年)的介绍治疗健忘症药物的《健忘症治疗药物》、卡塔尼(Kattani,西元951~1029年)的关于治疗体表疾病的《体表危险疾病的治疗》。贾扎尔(Jazzar,西元895~980年)不仅专为旅行者写了一本介绍疾病、发热、有毒昆虫与动物叮咬,以及在没有医生的情况下如何治疗与处置此类病症的书籍(拉丁版名为“Viaticum Peregrinantis”),而且作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他还非常热心于贫困人口的求医问药问题,《穷人医药》就是出自他的手笔。此外,有一位犹太医生(拉丁名为Maimonides,1135~1204年)发表了一本介绍痔疮的小册子,一位11世纪的基督徒巴特兰(Butlan)还写了一本治疗修道士疾病的书籍。它们都是用阿拉伯语书写的。
关于从医者的职业操守,(伊斯兰哲学家、宗教学者)伊本•;哈兹姆(ibn Hazm,西元994~1064年)提出,一个做医师的人必须在道德上具有良好的品质,即仁慈、富有同情心、友善、忍辱、接受负面批评;他对医师外表的要求是,医师应该留短发,勤剪指甲,穿戴干净,举止尊严。
在药物学方面,阿拉伯帝国的医生与药物学家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与大量的创新。他们善于使用复方制剂,主药、佐药与替代药巧妙搭配,首先开始将樟脑、氯化氨与番泻叶等作为药物加以使用;在他们的处方里,还出现了来自中国、东南亚、喜马拉雅山脉以及非洲的药物;而糖浆、软膏、搽剂、油剂、乳剂或脂等剂型,以及丸药的金、银箔外衣则是他们首创的,甚至今天西方医学界使用的“Syrup”(糖浆)、“Soda”(苏打)等词汇,都是从阿拉伯语音译的。当时的医学百科全书或综合性医学书籍都留有专门的章节介绍药物以及处方药物的搭配。这部分章节系统地讲解了药物与处方的构成成分与配制的程式和步骤。
伊本·贝塔尔(ibn al’Baitar,1188?~1248年)是中世纪最伟大的药用植物学家,他编写了两部医药学著作《药物学集成》与《医方汇编》,堪称经典之作,其中药物是根据它们的治疗作用进行编排的,而且除了阿拉伯语名称之外,还加上了希腊语和拉丁语名称,从而促进了医药学知识在欧洲的传播。《医方汇编》的拉丁语译本的若干部分,1758年还曾在义大利的克雷默那出版。
穆斯林的药物学成就对欧洲具有不可或缺的影响,后来相当长时期内欧洲这方面的著作,主要就是在先前穆斯林著作的基础上编辑或是稍做改编而成的,例如约翰尼斯1250年完成的《Expositio Supra Nicolai Antidotarium》(分别于1495、1599和1602年在威尼斯出版)。阿尔巴诺(1306~1316在帕多瓦任教)的《Conciliator and De Venenorum Remediis》则是广泛承袭伊本·拉希德等人的著述。15世纪萨拉迪尼·阿斯柯洛的《Compendium Aromatariorum》(药剂师手册),在形式和内容上深受穆斯林医学家伊本·西那等人的影响。而17世纪晚期出版的《伦敦药典》,在编列的药物分类和剂型种类上也反映出受到穆斯林药物学影响的程度。事实上,欧洲人使用的药典一直依赖穆斯林的著作与资料,直至19世纪晚期。
在众多科学学科中,医药学是穆斯林的长处所在,这种地位的取得,与学科教育是分不开的,而早在阿拔斯王朝(西元750~1258年,中国史书称“黑衣大食”)初期,即西元765年,巴格达就建立了医科学校培养医药学人才。
阿拉伯帝国早在倭马亚王朝时期(中国史书称为“白衣大食”,西元661~750年)就在大马士革建立医院提供医疗方面的服务,但是有文献可考的世界上第一所正规医院是西元9世纪在阿拔斯王朝的巴格达建立的;大约经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又有5所医院在巴格达开业。而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初期医院,则是东征的十字军在伊斯兰世界开阔眼界之后,返回欧洲13世纪在巴黎建立的,与巴格达的医院相差约有400年的时间……西元931年,帝国还规定城市或医院的医生必须通过考试才可以开业行医(据说先前的罗马帝国也有城市医生需要通过考试的规定)。根据记述,西元10世纪初期那里已经建立起流动医院,日常在帝国的村庄提供医疗服务。巴格达最具规模的一所医院建立于西元982年,该院建院之初就拥有包括眼科医生与外科医生(含正骨医师)在内的25名医生,而到1184年,一位旅行家描述说,那所医院的规模就像是一个巨型的宫殿。
西元872年帝国在开罗建立的一所医院,它是迄今最早的为精神病患者提供医疗的医院;12世纪与13世纪,纳斯里医院和曼苏里医院先后在开罗建立。另外,努里医院是12世纪在大马士革建立的。
相对而言,在穆斯林管理下的西班牙,医院出现的比较晚一些。
帝国的医院在设计上即为其赋予了非常完善的功能。目前了解比较多的是关于西元12~13世纪叙利亚与埃及的医院的情况。那里的医院在布局上呈纵横交叉垂直形状,中央部分是4个拱形大厅,比邻有药房、储藏间、图书室、工作人员生活区以及厨房,每个拱形大厅都有喷水池提供干净的水源。不同的疾病,诸如胃肠道疾病尤其是痢疾与腹泻、风湿性疾病、外科疾病、眼科疾病和发热等各自在不同的区域就诊,而女性患者则是在独立的诊室与病房就诊的。医院还为精神病开辟专门的病房。医院不仅配置正常的执业医生与药剂师,而且安排有值班医生接诊预约定时复诊的病人。当时的医院同时具有医学教学功能,并且有管理、护理与勤务人员从事工作,还有医学生为非专业人员提供相应的培训。
所有医院的建立与运营在财政上主要依靠的是国家预算,这笔预算来源于国家(向富人)征收的遗产税;另外,富人与统治者的捐赠也为医院提供了资金(伊斯兰教教义要求,生活宽余者,应该用部分节余说明穷人,给予的可以是实物也可以是金钱,即交纳“天课”)。虽然独立的行医者是收取一定的费用的,但是医院的服务据说是免费的。
4、化学
除了在数学、天文学和医学等学科收获颇丰之外,阿拉伯帝国的学者还是化学这一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其中哈扬(Jabir ibn Hayyan,西元721?~803年,欧洲人也称之为Geber)与前文提及的拉齐(al’Razi,欧洲人称其为Rhazes,西元865~925?年)被认为是“化学之父”。
化学源自炼金术,据说埃及法老时期就产生炼金术了,中国的炼丹术与之有一定关系。西元7世纪,上述技术与古希腊思想相融合而形成阿拉伯炼金术及阿拉伯化学。阿拉伯炼金术及阿拉伯化学后来传入欧洲,逐步演进为近、现代化学。
哈扬在化学实验中确立了实验法的重要地位。他不但首先发现几种化合物,还掌握一些化学物质的制备技术,例如制备硫化汞与五氧化二砷,制备近乎纯净的硫酸盐或明矾、堿等化合物,使用酸来溶解某些惰性金属如金、银,以及精通金属冶炼包括黄金提炼术。此外,他还通晓制作染布与皮革的染料与防水布的防水涂料,制造一种可以阻燃的纸,以及在夜晚看得到的墨水。我们现在仍在使用的一些化学术语例如“堿”,就是这位化学家发明的。
尽管他有时被当作一名炼金术士,然而他似乎不太热衷于制取贵重金属(将“贱”金属转化为“贵”金属是通常的炼金术士所追求的),取而代之的是,他努力开创基础性的化学方法以及研究化学反应本身具有的内在机制,从而将化学从炼金术发展成一门科学。他强调在化学反应过程中,各种参与反应的物质的量是一定的,这或可被看成是“定比定律”的雏形。
据信他一生写作了约100多部论着,在这些著作中约有22部是关于化学与“炼金术”的。它们被翻译成包括拉丁文在内的多种欧洲语言在欧洲的大学里讲授。译成英语的就有《Book of Kingdom》、《Book of Balances》及《Book of Eastern Mercury》等。许多哈扬(及其它化学家)的著作当时是不署名的,因此人们无法准确地估计其数目。17世纪英国翻译家里查德•;拉塞尔(Richard Russell)认为,英译名为《Sum of Perfection》的著作的作者就是哈扬。
不过在哈扬之后,据说也有一些他人的文稿假托哈扬之名。
虽然在哈扬的某些著作中体现的宗教与哲学观点业已受到批判,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哈扬的主要贡献在于化学领域而非宗教与哲学。他在化学领域的各种开创性成就——首次制取各种酸,尤其是硝酸、盐酸、柠檬酸、酒石酸,以及对于实验法系统性的强调,这些都是非常卓越的。他对化学的基础性贡献包括发明一些科学的化学实验方法,诸如蒸馏、结晶、煆烧、升华、蒸发等,以及一系列与之相应的实验仪器和设备。哈扬之所以被公正地看成是现代化学之父,正是基于他这些卓越的工作。因此,德国的梅耶哈夫教授说,欧洲化学的发展可以直接追溯到哈扬。
拉齐不仅是医学家,而且还是享有盛名的化学家。他继承了前者的炼金术理论及化学实验的传统,并与药物学研究相结合,使得化学理论和实验法继续发展。他在《秘典》(又译《炼金术的秘密》或《秘密的秘密》)一书中首先确定许多化学概念,把已知的物质分为四大类:植物、动物、矿物和衍生物,同时介绍了物质的“原子”构成学说并讲解了炼金术的原理,还对化学实验仪器与使用方法做了详细的记载。拉齐的《秘典》记载了化学反应步骤以及他本人从事的一些化学实验,这些实验包括蒸馏、煆烧和结晶等内容。拉齐的一些具有创新性的实验在《秘典》中都有反映,包括熔解金属的方法、水银的升华、苛性钠的制取、白降汞溶液的使用,以及从橄榄油制取甘油等。希尔指出,拉齐的《秘典》犹如一部实验指南的雏形。在拉齐的实验室里有许多今天仍然使用的实验设备,例如坩埚、分流器、蒸馏瓶、曲颈瓶、带有导管的蒸馏塞以及各种类型的加热炉等。
阿拉伯帝国的一大批学者乃至从业者在许多技术发明创新方面显示了无穷的才能与智慧,他们已经掌握了在当时算是独一无二的化学技术。而由杰拉德(Gerard,西元1114~1187年)12世纪在西班牙托莱多翻译的一部穆斯林学者的书籍(译作“De Aluminibus”),则讲述了氯化汞的合成步骤。他们还将化学知识应用于生产与制造,例如当时的制革以及玻璃、墨水、油漆、染料、焊料、粘合剂和人造珍珠等的加工和制糖等,其中许多东西与后来的工业具有直接的关联;他们将含糖与淀粉的物质发酵后通过蒸馏的方法制取酒精,比欧洲人早了300多年。今天人们使用的“alchemy”(炼金术)和“alcohol”(酒精)等词汇,都是取自他们的发明,而“chemistry”(化学)一词则是去掉“alchemy”的词头“al”之后衍生出来的。他们还发明了肥皂的制作方法。肥皂一词阿拉伯语读作“shabun”,西班牙语与葡萄牙语的肥皂(sabon),甚至法语的肥皂(savon),都是来自阿拉伯语,依此类推,英语的肥皂(soap)和洗发香波(shampoo)来源也大致若此……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另外,学者们开展化学实验的同时也带动了制药水准的提高。
亨利·莱斯特评价说:“在实用方面,他们(穆斯林——笔者注)发现了卤砂(氯化铵),制出了苛性碱,认识到动物性物质的特性和它们在化学上的重要作用。他们对矿物性物质的分类,已成为后世西方世界采用的大多数理论体系的基础。阿拉伯炼金术士在化学方面的功绩,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通常估计。他们对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化学的历史背景》)
精通科学史的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居斯塔夫·勒朋(Gustav Lebon,1841~1931年)的结论是,正是因为阿拉伯帝国科学家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执着的科学精神,才使得现代化学得以产生
5、物理
阿拉伯帝国时期穆斯林在物理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主要在于光学、力学(和动力学),以及对物质本质的认识。在力学方面,他们对物理学上的运动与惯性、时间与空间的概念的认识,和对抛物运动和重力作用的研究,为以后经典力学的建立做了必要的铺垫。他们还有人认为在世界产生以前,原始状态的物质是由具有空间范围的、分散的“原子”构成的。在光学上阿拉伯帝国的物理学家提出了光线来自观察的客体,认为光是以球面形式从光源发射出来的,进而认识光线的反射和折射现象。
伟大的物理学家金迪(al’Kindi,西元801?~873年,同时还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化学家和音乐理论家),一生至少着有265部以上的学术著作,但是传世的只有15部拉丁文译本。它们是关于气象、比重、潮汐、(几何)光学,以及音乐理论等方面的论述,许多内容是与物理有关的。
塔比特(Thabit ibn Qurrah,西元826~901年,兼数学家)是静力学的奠基人,他写了一部研究杠杆的力学著作——《杠杆的平衡》。他在该书中成功地证明了杠杆的平衡原理。
比鲁尼(Biruni,西元973~1050年)研究过流体静力学与物体的瞬间运动与加速度;他不仅发现光的传播速度快于声音,精确地测定了不同类型宝石的比重,并且为所有已知的复合物与物质元素建立了比重表,例如他测得金的比重为19.05~19.26,铜为8.72~8.83,水银为12.74~13.59,与实际值相差不大,另外,还正确地解释了喷泉与自流井的成因……
伊本·西那(ibn Sina,西方人称为阿维森纳Avicenna,西元980~1037年)不仅是医学家,他还颇富独创性地定义了诸如杠杆、滑轮和滚筒等机械装置,并且把它们做了分类。倾角的概念也是伊本·西那提出的,藉以解释物体的抛物运动,而这正是亚里斯多德物理学的薄弱环节。
哈兹尼(al’Khazini)是继塔比特研究杠杆平衡的最重要的科学家;他还设计一种奇妙的“智慧秤”,这种称在没有砝码的情况下也能测量物质的重量和比重。为此他在1137年还写了一本书——《智慧秤的故事》。哈兹尼对比重的研究卓有成效。他发现空气具有重量,使得阿基米德的浮力定律在空气中也能适用。哈兹尼还发现并证明越接近地心水的密度越大,而英国人罗杰·贝肯(Roger Bacon, 1214~1292年)则是在哈兹尼之后发现同一现象的。哈兹尼知道物体在不同高度测量的重量是不同的,进而提出了一种重要的物理学思想——物质的(质)量不同于重量,而且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正比关系。
在光学研究中,哈森(al’Haitham或al’Haytham,西元965~1040年,欧洲人称为Alhazen)为光线的物理学特性及几何光学奠定了基础,被称作“光学之父”。他不仅说明光在同一物质中是沿直线传播的,还研究了光的反射和折射,并且通过实验指出,垂直穿透不同介质之间介面的光线是不弯曲的。他甚至拥有一台可以制作透镜与研磨镜片以供实验使用的车床。他在实验中不但研究平面镜、球面镜、柱面镜和抛物面镜,而且研究球面像差和透镜的放大率,例如哈森发现透镜的放大作用是由于光线穿过玻璃与空气的交界面造成的,进而设想正是玻璃的弧度(透镜曲率)导致放大作用的产生。大气折射也是他研究的范畴。在光学研究中哈森善于应用数学方法解决几何光学的问题。暗箱成像实验也是哈森设计的,以此他正确解释了暗箱的成像原理,因此约瑟夫•;黑尔甚至在《阿拉伯文明》一书中甚至将哈森评价为“照相摄影”的先驱。学习科学史的人或许了解著名的“哈森问题”,即在光源和眼睛位置固定的条件下,如何确定球面镜、柱面镜和圆锥面镜上的反射点。例如对于球面镜,哈森的答案是“平行于主轴的光线照射至球面镜之后,都反射于主轴之上”。他关于球面像差、透镜的放大率和大气折射方面的发现通过开普勒等人的介绍,对欧洲科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哈森的一项重要贡献是对视觉原理的阐释。在哈森以前,人们一直坚信古希腊学者柏拉图(Plato,西元前427~347年)和欧几里德(Euclid,约西元前3世纪)提出的“视觉是由于眼睛发射出光线照射于物体上而产生的”这一错误观念,而哈森的观点是——视觉是反射光线通过眼球的玻璃体后落在视网膜上才得到的,而图像则最后产生于大脑。
哈森一生写过大约92部著作,其中主要论题是关于光学、天文、几何或数学。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的著作还被译成拉丁语,启发着后来的科学学家进一步探寻光学的奥秘。《哈森光学词典》一书(或译作《光学之书》,7卷),西元1270年被翻译成拉丁语,译名为Opticae thesauraus Alhazeni,是当时继托勒密(Ptolemy,西元2世纪)之后光学领域最重要的科学成就,并且奠定了光学的基础
6、实验法
前文曾提及阿拉伯帝国科学家的实验法,在此进一步加以阐述。
一位当时的学者伊本·泰米亚(ibn Taimiyya,西元1263~1327年)在《逻辑辩驳》一书中写到:“归纳法是在可靠的论证过程中产生的,并最终导致了观察和实验法的产生。”
古代希腊人学习科学知识的途径主要是通过思考、推测与推理。尽管希腊科学在当时取得过极其辉煌的成就,然而这种方法也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事实上,正是阿拉伯帝国的科学家们首先在科学研究中有条理地批驳以亚里斯多德为代表的希腊哲学思想,于是人类的科学研究活动开始生长出理论与实践的两只翅膀,进入不同于希腊科学的一个时代。
有一位西方评论家写到:“仅仅凭藉思考是不能发展科学的;科学的进步蕴藏在对自然研究的实践之中。实验与观察是他们(阿拉伯人)研究方法的本质特点……在他们的著作里,解决问题的方法总是通过做实验与进行实验观察获得的。”
哈森在《哈森光学词典》中明确指出,他的发现就是源自在实验中获得的证据。换句话说,其光学研究是建立在科学实验而非抽象的学说的基础之上。事实上,这正是现代科学研究的方法,也是穆斯林与希腊前人的本质区别。哈森的实验不仅系统性强且具有定量性,而且是可重复的。他总是设法获得实验资料之间的联系,或者说从实验结果中归纳出学说和理论,并且把后者用数学形式加以表达。假如学说和理论适用于那些实验资料,他就继续进行进一步的实验以期发现新的结果。
出于一种误解或排斥,一些欧洲人极力否定阿拉伯帝国科学家在实验法方面的地位,并且试图把开创实验法的荣耀与光环留给欧洲人自己。不抱偏见的科学史学家的研究表明,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早在1000多年前就建立了科学研究的实验室从事科学实验,并且将诸多科学发现加以公布。
作者罗伯特·伯瑞弗尔特(Robert Briffault,1876~1948年)在《构建人性》中写到:“牛津大学的继承者罗杰·贝肯曾经学习阿拉伯语和阿拉伯科学,他不仅是穆斯林科学的信徒,而且将阿拉伯文和阿拉伯科学作为唯一的真知向他的同代人不厌其烦进行传播和宣扬,并讨论实验法的渊源,澄清欧洲文明的源泉等。可以认为,阿拉伯人的实验法就是由贝肯在他那个时代热诚地在欧洲广泛加以传播的。”其实早期的西方大学,如牛津大学与巴黎大学都有阿拉伯系,罗杰·贝肯(Roger Bacon,西元1214~1292年)就一度是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的阿拉伯系研究学者或学生。他曾经长时期在西班牙的穆斯林科学之城托莱多留学与从事科学翻译工作,并把许多科学著作带回到英国。
从上段引文中人们不难看出,阿拉伯实验科学通过这位生活在13世纪的欧洲人对后来的义大利人伽利略(Galileo,西元1564~1642年),或者还有英国人法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西元1561~1627年)确定科学实验的地位不无影响。事实是,后人所说的(法兰西斯)培根哲学(Baconian Philosophy),或曰科学研究方法的三步骤——观察、实验和归纳,很早以前就被阿拉伯帝国的学者广泛采用。
包括现代自然科学在内,科学无一不是建立在“观察事实,用分析和实验加以证实,进而建立科学的法则”的基础上。因此实验法在科学中的地位是不可或缺的。
实验法,或称其为实验科学,是帝国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手段。借助实验法,他们能够在已知或完全未知的科学领域打开全新的视野,取得重大的突破。因此,这种建立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视野与突破,不仅本身就是科学编年史上黄金一样的篇章,而且为现代自然科学的产生铺垫了唯一的道路。
根据哈森的光学理论,穆斯林学者还成功地解释了彩虹的成因,即彩虹是阳光在经过大气水珠时发生折射和反射的结果。
阿拔斯·伊本·弗纳斯(Abbas ibn Firnas,西元?~888年)是研究飞行动力学的先驱。西元875年,他凭藉自行设计、制造的“飞行器”在科尔多瓦城居民的目睹下尝试“飞行”(滑翔)试验,经过一段距离的滑翔之后,着陆时背部严重受伤,被誉为“飞行第一人”(西元852年摩尔人阿蒙·弗曼穿着翅膀样斗篷从科尔多瓦的一座尖塔上纵身跳下尝试“飞行”,落地时受轻伤)。这比义大利人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年)大约早了600年的时间。
其他还有Barlu Musa、al’Naziri、ibn Jami、al’Attar、Abdur Rahman ibn Nasr等人,都是从事过物理学研究的卓越的科学家;而且穆斯林还是钟摆的发明者〔钟摆是天文学家尤努斯(也译作尤尼,ibn Yunus,西元950?~1009年)发明的〕,库特比(Kutbi)发明的钟表还曾被当时的哈里发作为礼物赠与法兰克国王查理曼(Charlemagne,西元742~814年)。
7、生物学
阿拉伯帝国生物学家对生物学的发展做出过杰出贡献,帝国的学者、技术人员乃至劳动者专长于植物学、园艺、农业以及动物学知识或技术,尤其是西班牙的穆斯林把植物学、园艺、农业研究推向了巅峰状态。
西班牙穆斯林植物学家采集大量植物标本加以系统性与科学性研究,并亲自对栽培的植物进行分类。这或许是仰仗了伊比利亚半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他们还发现同种植物之间,如棕榈和大麻各自存在性别差异。
迪纳瓦利(al-Dinawari,西元?~895年)是穆斯林治理下西班牙的一位伟大的植物学家。他以6卷的篇幅(《植物之书》)记录与描述了大量关于植物的论述,例如各种植物的特性与品质、生长过程与生长周期,以及植物对于土壤的不同要求。迪纳瓦利研究的植物品种极其繁多,仅在其残存的两卷著作中,就涉及植物约400多种(包括农作物及水果),而且还将植物学与天文学和气象学知识结合起来。
12世纪末出生于西班牙马拉加的伊本·贝塔尔(ibn al’Baitar,?~1248年)堪称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植物学家(兼药物学家,见前文“医药学”部分)。其足迹遍布西班牙、北非与小亚细亚等地中海地区。他记录与描述的药物达1400多条款,包括大量的药用植物与蔬菜,并且著录成书《医方汇编》,其中首次介绍了此前不为人所知的200种新的植物。此书部分内容于1758年还在克雷默那被翻译成拉丁语出版(见前文医药学部分)。
著名的植物学家伽菲奇(al’Ghafiqi,?~1165年),也对许多采集于西班牙和非洲的植物标本进行精确的记录与描述,并且用阿拉伯语、拉丁语与柏柏尔语等不同语言命名植物。
其他还有Abdul Abbas al’Nabati、ibn Sauri、ibn Wahshiya、Zakariya al’Kaiwini、ibn Maskwaih等人,也都是那个时代杰出的植物学家。
穆斯林对植物学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今天,在西方的语言里许多植物仍然沿用由阿拉伯语衍生的名称,例如红花、苜蓿等。
园艺也是穆斯林的至爱所在。植物学成就的取得,不仅促进了农业水准的提高,而且带动了园艺学的进步,翠绿的植物园与修剪得体的花园遍布巴格达、开罗、非斯(位于摩洛哥)和西班牙的科尔多瓦等地,历史上的田园诗人曾经将它们比作人间的天堂。在西班牙、西西里和法国部分地方,即当时曾经处于阿拉伯帝国统治或伊斯兰文明影响的欧洲地区,即使今天人们仍然可以发现一些穆斯林园艺遗产或与之有关的文明古迹,例如格拉纳达的爱尔罕布拉宫(别名“红宫”)花园。而且以爱尔罕布拉宫花园为代表的西班牙园林,更成为欧洲园林的典范。《历史上的花园》一文的作者威廉·霍珀也对这座花园给予热情的肯定,而且在谈及中世纪欧洲其它地方的鲜明反差时,霍珀则干脆直言,其它地方简直是满目荒凉。
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1884~1956年)说:“园艺学的改进构成了伊斯兰最好的遗产。西班牙的园丁盛赞这是泥土最高贵的品德。园艺学的发展,使农业得到空前的繁荣,这也是西班牙穆斯林的荣耀之一。”
奥旺(ibn al’Awwam,12世纪)的《农业之书》是介绍农业与畜牧业的著作,可谓代表当时农业水准之集大成者。此书讲述了585种植物和50种果树的栽培与嫁接技术。他不仅讲解了不同性质土壤的不同施肥的方法,而且讲授了农业灌溉、作物杂交与多种植物疾病及其治疗方法。
巴萨尔(ibn Bassal,11世纪)进行了土壤分类方面的研究,他把土壤划分成10种类型,并且分析了土壤活力与季节变化的关系,以及不同土壤与作物对翻耕次数的不同要求。
在西班牙,穆斯林铺设了纵横交错的灌溉网路,从而保证了农业的丰产丰收。在安达卢斯地区,他们创造的这种奇迹使得那里被历史学家称作人间天堂。德弗纽克斯在他的著作——《黄金时代西班牙的日常生活》中写到:“最值得称颂的地方位于格拉纳达一带,摩尔人曾经长时期生活居住在这片自由的王国。他们通过水渠和隧道将水从白雪覆盖的山峦引来浇灌平原及其周围鲜花盛开的山坡,从而使得那里成为具有世界上最美丽景色的地方之一。”的确,即使是今天的西班牙仍然受益于当年穆斯林修建的水利基础,而西班牙语里大量的诸如水渠、水池、灌溉税等来自阿拉伯语水利方面的词汇,则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穆斯林留下的历史烙印。
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穆斯林把品种众多的农作物带到欧洲,它们包括甘蔗、棉花、茄子、柑橘、香蕉、海枣、洋蓟、番红花等,而穆斯林的欧洲邻居们,从他们那里学会了这些东西的称谓,例如西班牙语的棉花一词——algodon,就是来自阿拉伯语(al’qutn),英语的棉花——cotton,亦来源于此。虽然水稻最早据称是罗马人引入欧洲的,但是那时却从未大规模种植,而是后来由穆斯林在建立了科学的灌溉系统的基础上,大量引进与栽培的。穆斯林在欧洲推广水稻的路线,首先是西班牙、西西里,然后是义大利的比萨平原与伦巴第地区。这些作物后来又被欧洲殖民者带入美洲。
这些成果对于当时提高农业生产水准,解决人口的吃饭问题至关重要。鼎盛时期穆斯林治理下的西班牙面积占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或1/2强,在单位面积内养活的人口远远高于所有其它欧洲国家。创造这种奇迹没有先进的农业技术的保障是根本不可能的,而这一切却发生在西班牙,发生安达卢斯,发生在穆斯林治理西班牙的7~8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之中。
出生于阿拔斯王朝(西元750~1258年,中国史书称“黑衣大食”)巴士拉城的贾希兹(al’Jahiz,西元776~869年)不仅是世界上第一个记录鸟类迁徙的动物学家,他写的一本介绍动物的书籍(《动物之书》),已经包含有动物心理学与社会行为的内容,尤其是还包含有进化论的萌芽。在动物的物种分类方面,他首先把动物以从简单到复杂的链条穿起,并且根据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划分出不同的类别,然后再进一步划分出亚类……如此分类下去直至终末。他发现环境因素对于动物生活的影响,以及动物在一些因素的作用下而发生的变化。
对于动物的“进化”机制,贾希兹提出了3个方面的学说,即,生存斗争、物种变化,及环境因素。
按照作者的观点,这种生存斗争便是不同的个体彼此之间进行的“战争”,强者以弱者为食,弱者努力保护自我,这是造物主的法则。他还以鸟、大鼠、蛇、海狸、狐狸、鬣狗等为例来说明他的这种法则。例如,他说大鼠外出搜寻食物,捕食比它弱小的动物比如鸟,它同时需要隐蔽自己与幼子以躲避蛇的掠食。在贾希兹看来,这种斗争不仅在不同的物种之间存在,在相同的物种之间也是存在的。生存斗争其实就是一种自然的选择,这是出于动物自我延续的天生的本能。
贾希兹认为,物种变化与变异是有可能发生的,环境因素也参与其中。他宣称,原物种可以通过逐渐产生新的特征而衍生出新形式的物种,这种新的特征有助于其在所处的环境下生存。贾希兹在谈及四足动物的时候说到:“有人能够接受四足动物祖先的进化学说,并且认为狗、狼、狐狸以及与它们类似的动物都是由这种祖先产生的。”
至于环境因素,他提出食物、气候、居所等要素对于物种具有生物学与心理学方面的影响。
贾希兹把物种变化的主要动力归结为造物主的意志。
贾希兹是历史上最早提出“进化论”的生物学家,他在动物学乃至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在后来穆斯林世界以及欧洲的生物学家身上产生不可磨灭的印记,例如瑞典的林内乌斯(Linnaeus,1707~1778年)、法国的布丰(Buffon,1707~1788年)与拉马克(Lamarck,1744~1829年),以及英国的两个达尔文(E. Darwin,1731~1802年;Charles R. Darwin,1809~1882年)。由此读者不难发现,达尔文(Charles R. Darwin)的《物种起源》不是凭空产生的,换句话说,达尔文并非是从零开始的。
阿布·乌拜达(Abu Ubaidah,西元728~825年)对马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总共写过100多部著作,其中有一半多是关于马的。
埃及的达米利(al’Damiri,?~1405年)则是穆斯林世界最卓越的动物学家。他关于动物学的百科全书——《动物生活》,对动物发展史的介绍比布丰早了几百年。
8、地理学
阿拉伯帝国时期的地理学内容极为丰富而详实,既有绘图学与海上探测的知识,也有旅行家对山川地貌的记录,还包括测地学如对地理学座标甚为精确的数学测量与定量的地貌研究。学者的地理学知识不仅借鉴古巴比伦、印度、波斯与希腊的成果,而且建树颇多,对之后航海时代的到来具有重要意义。他们绘制的地图是继希腊人之后对世界的最重要的认知,并具有质的进步,与中世纪欧洲基督教世界通行采用的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寰宇图”则有天壤之别。
穆斯林的信仰要求人们开拓心智与视野,以及探究造物主造化的神奇,因此广袤的土地无法羁绊他们走出去的脚步。旅行家与学者的长途旅行与考察是畅通的,即使是跨越帝国之中相互敌对的区域也是如此,而且大部分旅馆依靠个人的捐款维持经营,并免费向旅行者开放。正如当时最杰出的地理学家比鲁尼(Biruni,西元973~1050年)所言,伊斯兰已经贯穿从东方到西方。
阿巴斯王朝(西元750~1258年,中国史书称“黑衣大食”)是今天所谓的“科学的地理学”的发端时期,因为自那时以来地理学便真正成为“定量加描述性地理学”。穆斯林学者不仅从印度天文学书籍里学习很多长度计算方法,而且还从希腊与波斯的著作中受益非浅,进而建立“定量加描述性地理学”。
地理学家在大地测量学方面颇有建树,如测定城市的方位、山峰的高度等,甚至在测量地球的半(直)径、周长、经度等方面,也做过有益而富有成果的尝试(假定地球为圆形)。
比鲁尼,堪称定量加描述性地理学即科学地理学的先驱,其代表作是原本用来确定穆斯林礼拜朝向的《城市方位座标的确定》。这部著作以及比鲁尼其它地理学著作的特点是,在地理学上追求数学的精确与论证的严谨,这与他深厚的数学及天文学功底是分不开的。事实上比鲁尼同时是以伟大的数学家与天文学家闻名的。他对地理学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发明了采用三角测量法测量大地及地面物体之间的距离的技术,并测量了地球半径,换算成今天通行的长度单位为6339.6千米,这与现在我们所掌握数值(赤道半径6378.140千米,极半径6356.755千米,平均半径6371.004千米)已经相差无几。他的贡献还在于对地球的经、纬度做出精密的测量,改进了经、纬度的测定方法,并且发明了测量山峰和其它物体高度的方法。比鲁尼总共撰写了15部大地测量学(或数学地理学)著作,《绘图法》是其青年时代的作品;《古代国家编年史》讲述的是古代各民族的历史和纪元,涉及很多地理知识,蒙莉莎媒体出版社甚至在1984年还发行出版过此书;《印度》介绍了关于印度的自然与社会知识,包括提供了那里丰富的地理学资讯。
比鲁尼可谓是中世纪地理学第一巨人,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1884~1956年)则干脆把11世纪(上半叶)命名为“比鲁尼的世纪”。
此外,历史上一幅著名的世界地图——“马蒙地图”诞生于西元9世纪初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马蒙时期(西元813~833年)。
有一部集宇宙天体、历史与地理于一体的百科全书——《黄金草原》,其作者马苏德(al’Masudi,西元895?~957年)是一位生活在(9~)10世纪的著名阿拉伯旅行家,在西亚、南亚、南欧和东非都遍布他旅行考察的足迹。《黄金草原》在以后数百年间被从事自然与社会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在学术著作中广泛引用。
伊斯兰教要求,在经济与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个穆斯林一生之中至少需要赴麦加朝觐一次,此外,穆斯林素有外出经商的传统,他们热爱旅行和探险,这些都对地理学的发展提出很高的要求并且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当时的地理学家利用他们掌握的天文学与数学知识,绘制出各种地图,出版了许多旅游书籍。
穆卡达西(Al’Muqaddasi,西元945年~?)是第一个使用自然色彩绘制地图的地理学家,他大约在西元985年完成并发表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地理学著作——《地域知识》。当代学者给予穆卡达西极高的评价,克雷默斯称:“那些在现代地理学中令人感兴趣的科目,没有穆卡达西未涉足的。”米克尔则称其为“所有地理学科的开创者”。雅库比(al’Ya’qubi)在进行了长时间旅行考察的基础上,于西元891年完成《国家》一书。该书详细介绍了各地区城镇与国家的名称、城镇之间的距离、地形地貌、水资源,以及百姓、统治者和税赋的情况。伊本·克达比(ibn Khurdadhbih,西元?~912年)是《交通与行省》的作者。此书绘制了穆斯林世界所有贸易线路的地图并给出了文字说明,介绍的贸易线路甚至远达东亚的中国、朝鲜和日本、南亚的雅鲁藏布江、安达曼群岛、马来亚与爪哇。曾经在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工作过的地理学家易德里斯(al’Idrisi,拉丁名Dreses,1099或1100~1166年)来自穆斯林世界,但后来就职于诺曼第人罗杰二世(Roger Ⅱ)的西西里宫廷。他编撰过以赞助人罗杰二世命名的《罗杰之书》(也称《世界地理》),并且绘制了一幅圆形地图——世界地图,以及制作了一架银质的天球仪,可谓那个时代的奇迹。内有70张地图的《直通天空台》一书也是他的作品。雅古巴·哈马维(Yagubal Hamawi,1179~1229年)则写作了内容翔实的《地理词典》。
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1304~1369年)是著名的摩洛哥旅行家,他在21岁的时候就离开家乡坦吉尔,从此开始了长达近30年的旅行。伊本·白图泰也许是在蒸汽机车产生之前合计旅行距离最长的旅行家。除了访问过西亚、北非和西班牙等所有伊斯兰国家和地区之外,他的旅行足迹还远至亚撒哈拉即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和东部非洲,南亚的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以及欧洲的拜占廷、南俄和中国等地。在中国的杭州、泉州(刺桐港)以及北京(元大都)等地都留下这位伟大的旅行家旅行、考察的足迹。
伊本·白图泰结束旅行返回摩洛哥之后,口述其旅行见闻,经过伊本·祖扎伊·卡尔比(ibn Juzay al’Kalbi)三个月的记录与整理,而成《伊本·白图泰游记》。这部旅行家笔录,以丰富翔实的资料,成为介绍中世纪地理、历史、民族、宗教、民俗等方面一部价值极高的著作,长期被许多学者研究、引用。
指南针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把指南针加工成罗盘用于航海则是穆斯林的创造,这也为海上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技术基础。
从西元10~11世纪开始,伴随海上贸易的发展,海洋地理学揭开了新篇章。穆斯林航海家、水手、商人与传教者扬帆远航,足迹遍布四海重洋。除了去往欧洲之外,他们越过今天的印度洋,进入太平洋,抵达南洋群岛的爪哇、苏门答腊、吕宋,最后来到中国,甚至可能先于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46?~1506年)500年从西班牙及西非到达美洲。穆斯林们在与大海为伍的同时,积累了丰富的海洋地理学知识。他们熟悉航行的各个不同的海域,认识台风的威力,掌握季风的规律。这些与地理学有关的知识随着他们的足迹传播到东、西方,为后来的航海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例如气象学术语“typhoon”(台风)一词,便是来源于阿拉伯语音译“tufan”,“monsoon”(季风)一词则是源自“mawsim”。
三、文献翻译
阿拉伯帝国在推进疆界的同时,继承了大量先人的科学文献。帝国不但很好地保存这些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而且还着手进行意义重大的文献翻译工作,包括翻译几乎全部的希腊著作。
在倭马亚王朝(中国史书称为“白衣大食”,西元661~750年)时期,就有部分翻译家自发地翻译用古叙利亚语——阿拉马语书写的医学与天文学著作。但是,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一般还不是在中央政府的统一规划和组织下进行的。
自西元750年阿拔斯王朝(西元750~1258年,中国史书称“黑衣大食”)建立后,随着对外征服活动的减少,社会趋向于安定,经济进一步发展,科学文化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文献翻译活动也得以大规模进行。历史学家通常将这一时期称作伊斯兰及伊斯兰科学的“黄金时期”,其中以哈里发马蒙时期(西元813~833年)的翻译工作尤为突出,都城巴格达于是也成为举世闻名的科学翻译中心。历史上著名的“智慧宫”就开始兴盛于哈里发马蒙时期。“智慧宫”是一所集图书馆、科学院和翻译局于一体的综合性图书馆及科学研究机构。在政府的主持下,当时一流的专家、学者聚集于此,把包括科学图书在内的大量古埃及、希腊、罗马、波斯和印度的古籍翻译成阿拉伯语。马蒙热心于赞助科学文献的翻译工作,据说他曾以与译稿等重的黄金酬谢著名翻译家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Hunayn ibn Ishaq,西元809~873年,欧洲人称之为Joannitius,兼翻译家与数学家,基督徒)。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曾经游历于希腊语国家收集资料与手稿,并将大量有价值的文献翻译、整理及保存下来。
阿拉伯帝国的学者并没有满足于通过翻译所获得的知识,或者说他们的工作绝非简单的翻译与被动的接收,而是校正了很多的古籍的错误与不足,并进行深入的考证与细致的诠释和评价,进而创立自己的科学理论。这可谓是帝国科学的显著特点之一。
阿拉伯帝国的翻译家的辛勤劳动也为人类留下了珍贵的遗产,这些遗产后来又通过帝国版图上的西班牙、西西里和法国部分地区传遍欧洲,成为点燃文艺复兴的文明的火种。
四、阿拉伯帝国与中华文明的交流
阿拉伯帝国与中国的科学与文化交流在帝国建立之前的很长时间就已经存在了。以伊斯兰文明为特征的阿拉伯帝国兴起后,恰逢中国历史上科学技术发达的大唐王朝与两宋,因此两种文明的交流与借鉴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况且帝国的穆斯林向来有四海为家的传统。
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曾经告戒他的弟子说:“知识即使远在中国亦当往求之。”据《旧唐书·西域传》记载,唐高宗永徽二年(西元651年),大食国(阿拉伯帝国)第三任正统哈里发奥斯曼(Uthman ibn Affan,西元?~656年)派遣使节抵达长安与唐朝通好,唐高宗即为穆斯林使节赦建清真寺。此后双方来往频繁,见于我国史书记载的,大食使节来华次数至少达37次之多。安史之乱暴发后,西元757年唐朝向大食求援,大食即派遣军兵帮助平定安史之乱,这些人后来也大多留在了中国成为中国回回人的先人之一。
西元8世纪中叶,中国的杜环(在怛逻斯战役中被俘)去过阿拉伯地区,足迹远至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摩洛哥等地,并且将其所见所闻写成一本书——《经行记》,不仅为中国人了解阿拉伯帝国及穆斯林世界打开了一扇视窗,也为中、阿文明交往留下珍贵的资料。可惜杜环的《经行记》原书失传,但是其族叔杜佑在所著《通典》中摘引数段;此外《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通志》和《文献通考》亦有少量转引。
中国的“四大发明”最早传出的是造纸术。西元8世纪,也就是在大食第三任正统哈里发奥斯曼派遣使节来大唐的大约100年之后,外部世界的第一个造纸作坊就出现在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附近)。《旅程和王国》一书有这样一句话——“纸是由俘虏自中国引入撒马尔罕的。”这里所说的俘虏即指在怛逻斯战役中被俘的一些中国造纸工匠。在时间上前后几乎相差无几,巴格达也出现了造纸作坊,之后逐渐扩展到大马士革、开罗,以及摩洛哥与西班牙的一些城市。巴格达也好,撒马尔罕也好,造纸技术全部都是由来自中国的造纸工匠传授的,而且这种技术后来又被传往欧洲。中国的造纸工匠除了在怛逻斯战役中被俘后流落它乡传播造纸技术,也可能是作为文化交流使者在怛逻斯战役之前就到达了那里,或者兼而有之。另外,在西元8世纪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西元750~1258年,中国史书称“黑衣大食”)的大城市里,已经出现来自中国的绫绢机杼,并且还有来自中国的技师(金银匠、画匠及纺织技术人员等)在当地工作,例如京兆人樊淑、刘泚为“汉匠起作画者”,河东人乐×、吕礼为“织络者”〔(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九十三》〕。
继造纸术之后,一些中国的其它发明创造也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传进阿拉伯帝国,后来通过帝国版图上的西班牙、西西里和法国部分地区传遍欧洲,对西方的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文明的交流是互相的,伴随科学与文化交流的发展,不仅伊斯兰教传入了中国,而且阿拉伯帝国先进的数学、天文历算、医药以及航海、地理知识为中国人所了解。例如,他们先进的医药学知识大大丰富了中医药学的内涵,我们今天所能使用的中药,相当一部分就是当年穆斯林商人与医药学家从阿拉伯、波斯与印度等地引进的“海药”(唐代官员已经开始用文字记载这些影响)。而且帝国来华的穆斯林自唐代以来,已有人开始长期在长安、广州、泉州、杭州、南京、扬州及北京(大都)等重要城市居住,直接参与中华文明发展的进程。正是由于受到这种外来文明的影响,中国人便开始认识、学习伊斯兰科学,例如13世纪元代的穆斯林天文学家札马鲁丁引进、设计、制造的世界上罕有的地球仪等7种天文仪器,进而明代的郑和船队在15世纪甚至开创了七下西洋的壮举……
伊本·纳迪姆(ibn al’Nadim,西元?~999年)在《科学书目》中,还记录了阿拉伯帝国著名医学家拉齐(al’Razi,欧洲人称其为Rhazes,西元865~925?年)帮助一位中国医药学家的故事。这位在巴格达学习并且住在拉齐家里的中国医药学家,在回国之前请求拉齐为他读盖伦医学著作的16卷阿拉伯文译本。拉齐满足了他的要求,他则以中国的“速写法”(草书)记录全文并将之带回中国。20世纪英国的科学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年)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也采纳了这个故事。
海上丝绸之路大约兴起于西元9世纪初,这也是维系两种文明交流的纽带。西元10世纪,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与航海家伊本·瓦哈比的商船由巴士拉与西拉夫(古代波斯湾港口)经海路驶进中国的广州港。之后,他们对于中国风土人情的大量的叙述(由阿布·赛义德·哈桑整理出版),使得当时的阿拉伯世界进一步认识了中国。此类故事或许也为阿拉伯名著《一千零一夜》提供了与中国有关的素材。
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融会贯通、互通有无、彼此借鉴,共同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这种文明的交往堪称人类一切文明交往的典范。
五、关于焚烧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谎言
现在让我们来戳穿一个关于穆斯林征服者焚毁亚力山大图书馆的谎言,以便使“疯狂焚烧托勒密书稿”这样的寓言故事就此止步。
西元642年,阿拉伯军队在阿莫尔·本·阿绥的统帅下进入埃及的亚力山大城,一种传说认为阿莫尔奉哈里发欧麦尔(Umar,西元634~644年在位)之命将亚力山大图书馆放火焚毁。据传欧麦尔的理由是,如果这些希腊人的著作与安拉的经典一致,它们就没有保存的必要了,因为现有的经典已经足够了;倘若它们不一致,则是有害的,应该被摧毁。总之,毁灭它们是合理的。
居斯塔夫·勒朋(Gustav Lebon,1841~1931年)说:“所谓的焚烧亚力山大图书馆这样荒蛮的行为并不符合阿拉伯人或穆斯林的道德准则。人们会产生这样的质疑——那些杰出的学者们长久以来怎么会相信这样一种传说?这种传说遭到我们这个时代唾弃,根本没有再去讨论必要了。没有什么事情比证明在伊斯兰征服世界以前,是基督徒自己焚毁了异教徒的书籍更容易了。”
奇怪的是,那些穆斯林征服时代或稍晚一些的、人才济济的历史学家(包括埃及的基督徒历史学家例如Eustichius与Elmacin),一概保持缄默,没有一人留下对焚烧亚力山大图书馆事件的片言只语的记载,倒是过了大约500多年到13世纪突然冒出三个人讲起这个故事,其中尤以一个叫伊勃努尔·希伯莱(Ibnul al’Ibri,意思是“犹太人的儿子”)的人的说法经不起推敲。
按照这位“犹太人的儿子”的说法,那些被焚烧的70万册图书被亚力山大的4000座浴室当作燃料连续燃烧了半年的时间。但是,这种说法却出现了简单的算数问题——如果把按此人所说的70万册图书分送到4000座浴室,那么每个浴室只能分到175本,而要想让这175本书连续焚烧半年,则每本书至少需要持续燃烧一天以上。所以,人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疑问——什么样的书可以连续燃烧24个小时?况且多达70万册这一数量本身就是令人无法相信的。由此听众完全可以否定这个“犹太人的儿子”讲述的“寓言”的真实性了。
事实上在阿拉伯军队进入埃及以前,亚力山大图书馆几经破坏,并且至少被放了两次大火,一次在西元前47年,放火的是大名鼎鼎的朱利斯·恺撒(Julius Caesar,西元前101~44年)的舰队,另一次在西元391年,适值罗马帝国分裂前的最后一位暴君——狄奥多西(Theodosius,西元347~395年)统治时期,而等到西元7世纪阿拉伯人进入亚力山大城的时候,这座图书馆已经名不见经传,没有什么地位可言了。许多历史资料都提到这两次大火。莫非“犹太人的儿子”以那两次大火为蓝本,杜撰了一个新的寓言故事?
希提(Phillip Hitti,1886~1978年)在《阿拉伯通史》中也对这个故事持否定态度。他说:“巴格达人阿卜杜勒·莱兑弗(回历629年,即西元1231年卒)似乎是首先叙述这个故事的人。他杜撰这个故事的目的何在,不得而知;但是,后来的著作家,以讹传讹,把这种说法大肆渲染,好像实有其事一样。”
“每一个基督徒都被灌输以这个故事——哈里发摧毁了亚力山大图书馆。”贝特朗·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年)的一席话直接点明了西方人热衷于排斥“异教徒”的要害。他写到:“与不仅迫害异教徒,而且自相残杀的基督徒形成对照的是,穆斯林因宽宏而受到欢迎,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他们的征服活动。在后来的一些时候,对犹太人和摩尔人的狂热的憎恨毁坏了西班牙,法国也因对胡格诺教徒的迫害受到悲惨的削弱。”可见,在罗素看来,中世纪的西方人自己倒是蛮适合扮演放火者这一角色的。西班牙的费迪南(Ferdinand II,1452~1516年)和伊莎贝拉(Isabella I,1451-1504年)两位陛下,不就以把穆斯林与犹太人的书稿投进烈焰为荣耀吗?英国作家科林·威尔逊曾就西元391年亚力山大城主教在狄奥多西支持下,下令焚烧图书馆加以讽刺——知识是邪恶的,亚当就曾因为求知而被逐出伊甸园。有位教皇也有一句名言——无知乃虔诚之母。
当代一些人对于传播此类“烧馆”的故事乐此不疲,可能缘于盲信,但也不排除出于有意的动机。约瑟夫·巴纳巴斯甚至将“烧馆”的行为比做纳粹,有一位叫乔格的印度人则更加直白地表露说,穆斯林的所做所为完全是出自他们的宗教。看来有的作者似乎并不在意“烧馆”事件的荒谬与否,获得“穆斯林是科学的敌人”这种结论,才是他们的笔锋所向
六、地位与学者评价
当欧洲笼罩于基督教的黑暗之时,以伊斯兰为特征的阿拉伯帝国的文明光芒璀璨,成就斐然。对于这种文明的地位,权威的科学史学家的评价是,纵向来看,它在人类历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承前(希腊、罗马)启后(文艺复兴)的作用;横向来看,东、西方文明在此碰撞,水乳交融,相得益彰……
威尔斯(H.G. Wells,1866~1946年)写到:“由希腊人开创的对资料的系统性的积累,因伞族人(闪米特人,此处指阿拉伯人——笔者注)令人震惊的复兴而得以继续。亚里斯多德和亚历山大博物馆的种子久已沉睡,失去生机且被遗忘,如今开始开花结果了。”(《世界简史》)
而居斯塔夫·勒朋(Gustav Lebon,1841~1931年)则写道:“阿拉伯人迅速地创立了一种与以往的许多文化有着很大差异的新兴文明。由于他们良好的政策,使许多民族接受了他们的宗教、语言和文化,连具有古老文明的埃及人、印度人也不例外,他们情愿地接受了阿拉伯人的宗教信仰、传统习惯和建筑艺术……”
了解一些科学史的人都知道,历史上西方学者曾广泛使用阿拉伯文,或受益于阿拉伯帝国的科学文化,许多科学著作都是用阿拉伯语撰写的,帝国在此期间也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因此,前西德历史学家赫伯特·格特沙尔克在《震撼世界的伊斯兰教》一书中写到:“全世界都感谢阿拉伯语在传播中世纪高度发展的阿拉伯科学知识方面所带来的媒体作用……如果没有阿拉伯语这个媒介,得到这些知识是不可想像的,或者说无论如何也不会了解得那么早。”
历史学家希提(Phillip Hitti,1886~1978年)的《阿拉伯通史》有这样一段话:“如果我们把那些以阿拉伯语为母语的人视为阿拉伯人,而且地域不仅仅局限于阿拉伯半岛,那么在中世纪的第一个篇章里,就人类进步而言,没有任何民族做出的贡献堪与他们相比。除了远东之外,数个世纪以来阿拉伯语在整个文明世界作为学术、文化和知识进步的语言。”
作者罗伯特·伯瑞弗尔特(Robert Briffault,1876~1948年)在《构建人性》中则更加明确地说:“如果没有阿拉伯人,现代的欧洲文明就根本不会出现,这是极其可能的;绝对可以肯定,如果没有他们,欧洲便不会扮演那么一种超越所有先前进步阶段的角色。”“正是在阿拉伯与摩尔人文化的感召下……真正的文艺复兴才得以发生。正是西班牙而非义大利,成为欧洲再生的摇篮……”
居斯塔夫·勒朋还旗帜鲜明地指出:“十字军战争不是导致学术进入欧洲的主要原因,而是通过西班牙、西西里和义大利。”
《西班牙的摩尔人》的作者、英国人斯坦利·莱恩普尔(Stanley Lane-Poole,1854~1931年)说:“西班牙在穆斯林统治下的近8个世纪里,发展成为整个欧洲文明的光辉典范——当欧洲其它地方呈现萧条的时候,这个国度的艺术、文学与科学一片繁荣。来自法国、德国与英国的求学者聚集在这里,汲取这些流淌在摩尔人的城市里的知识的甘泉。”历史上,在西班牙科尔多瓦、塞维利亚与格拉纳达的高等学府里,云集着为数众多的基督徒与犹太学生,他们如饥似渴地向穆斯林学者学习科学,然后又把所学到的知识在欧洲播散。
以下引用当时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写给西班牙哈里发希沙姆三世(1027~1031年在位)的一封信函,他在信中请求哈里发允许他派遣王族成员前往科尔多瓦大学学习。
“乔治二世——英国、高卢、瑞典及挪威的国王,致西班牙穆斯林国王哈里发希沙姆三世陛下:
我们已经获悉,贵国之科学、知识、技术与制造业甚为发达,故,鉴于我们的国家在此类方面之匮乏,及全然处于愚昧无知,我们希望获得良机,以使我们的青年人受益于贵方之成就。
我们期盼这种良机可以让我们跟随你们的脚步前进,并以知识照亮我们的人民。鄙侄女杜邦特公主及一些英国贵族女子,希望受惠于你们的学术机构(科尔多瓦大学——笔者注)。对您特许给予我们机会以实现我们的目标致以敬意。
年轻的公主将为陛下晋献一份礼物。您若能够收下我们将倍感荣幸。
落款:您顺从的仆人——乔治”
西班牙穆斯林创建的大学也是后来一些欧洲早期的大学的模范,例如阿方索八世于西元1208年建立的帕伦西亚大学与弗雷德里克二世于西元1224年建立的那不勒斯大学。
尽管基督教世界翻译穆斯林的科学著作在诸如巴塞罗纳、里昂或图卢兹等地都有进行,但是占据首要位置的无疑是西班牙的托莱多。这座从西元8世纪至11世纪下半叶的3~4百年之间由阿拉伯或摩尔穆斯林治理的城市,开始成为整个欧洲的文化聚集之地,其声望尤其是在翻译工作大规模开展的12世纪以来,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在托莱多被译成拉丁语的穆斯林科学著作,至少应该有几百部以上或者更多。事实上,欧洲也因此而涌现出诸如桑塔拉的休(Hugh of Santalla,1119~1151年)、克雷莫纳的杰拉德(Gerard of Cremona,1114~1187年)、普拉托(Plato)、阿德拉尔德(Adelard,1075~1160年)、罗杰·贝肯(Roger Bacon,1214~1292年),以及贾斯特的罗伯特(Robert of Chester,成名于西元1145年)和荷尔曼等著名的翻译家。这些翻译家来自欧洲各地,他们云集于此,如饥似渴地从事科学著作的翻译工作〔在那些翻译家来到托莱多之前不久,那里甚至还出现了后来成为罗马教皇的吉伯特(Gerbertd Aurillac,西元945~1003年,即西尔维斯特二世——Sylvester II,任职999~1003年)的身影〕。《全球通史》也提到这些翻译家,它写到:“12、13世纪,这里的翻译家有犹太人、西班牙人和欧洲各地的外国学者。”可以这样说,他们来到托莱多的目的只有一个——尽一切可能获取穆斯林的科学知识。
事实上,自西元12世纪阿拉伯帝国学者的著作(和希腊、罗马著作的阿拉伯语译本)被大批译成拉丁语及其它欧洲语言以来,欧洲各大学将它们作为教科书长达几个世纪。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所谓的欧洲的“复兴”,又何尝不是穆斯林科学的传承。
科学的历史告诉我们,阿拉伯帝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承前启后,独步中古。如果将《构建人性》加以引申,人们就会明确无误地看到,彼时其科学技术与文化水准代表当时人类文明的最高境界。
阿拉伯帝国的文明在科学上多有建树,而且正是通过广大科学家与学者的创造性劳动,古代印度、希腊、波斯的科学巨著得以矫正并保存。
欧洲文艺复兴的大师们从阿拉伯语书写的科学巨著开始,点燃了复兴的火炬。如果没有崇尚科学的穆斯林的辛勤劳动,今天就不会有人看到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了;因为中世纪笼罩在欧洲的基督教的黑暗几乎摧毁了一切古代希腊的科学文化典籍,尽管衰败的拜占廷可能剩下典籍中的片言只语。不要轻视阿拉伯帝国科学的作用——当苟延残喘的拜占廷帝国几乎完全隔绝欧洲通向东方的道路之时,中国的“四大发明”是经由当时在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影响下的西班牙、西西里和法国部分地区,传往整个义大利乃至欧洲的;而奠定今日科学基础的文艺复兴,正是始于欧洲的这些地方。
对此,《伊斯兰的遗产》有所佐证。该书写到:“回顾历史,我们可以这样讲,伊斯兰(医学与)科学映射着希腊的光芒,当希腊科学的白昼流逝,伊斯兰(医学与)科学的光辉犹如月亮,照耀着中世纪欧洲最黑暗的夜晚……因为伊斯兰(医学与)科学指引或引导了那场伟大的运动(文艺复兴),所以我们有理由宣称这种文明依然与我们同在。”
流传下来的阿拉伯帝国科学的历史文稿有时是很粗略的,这使得一些人产生这样一种错觉,即它的科学只不过是对希腊科学在欧洲科学革命之前的一种保存。出现这种错觉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中世纪阿拉伯帝国的科学著作几乎都是以阿拉伯语书写的,今天的科学编年史学家真正精通这种科学语言的已经不多了,况且既精通语言又接受过科学训练的历史学家则更如凤毛麟角。另外,一些被翻译成拉丁语或其它语言的阿拉伯帝国的科学书籍,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有所变化和改动,读者已然很难分辨它们的渊源了。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在于,一些人有意或无意地进行了“模糊”处理。
但是,更有一些史学家力图歪曲史实,公然宣称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只不过是希腊、罗马文化的一点余光。”其实,这种蓄意抹杀阿拉伯帝国的科学地位与成就的鼓噪,不是出于无知,就是缘于偏见,并且以后一种可能性最大。而事实是足以胜过诡辩的。
诸如奥托·纽格堡(Otto Neugebauer,1899~1990年,奥地利)与德拉姆伯瑞(Delambre,1749~1822年,法国)之类所谓的学者甚至走的更远。例如在他们的报告里,伊斯兰天文学仿佛根本就不曾存在过,尽管那时的繁星也是像今天一样俯瞰着大地,然而穆斯林好像从来不曾凝视过星空。而皮埃尔·杜希姆(Pierre Duhem,1861~1916年,法国)的态度则可谓是滑稽可笑了。按着他的逻辑,中世纪的穆斯林在天文学方面同时身兼两重身份——一是疯狂焚烧托勒密(Ptolemy,西元2世纪)书稿的暴徒,二是毫无建树地模仿希腊科学的抄写员。可是,一个抄写员如何能够眷抄一部已经投进烈焰的书稿?这就好比让皮埃尔·杜希姆先生用自己的脚掌抽自己的嘴巴一样困难。前文对穆斯林焚毁亚力山大图书馆谎言的戳穿,已足以令皮埃尔·杜希姆之类的“伪术士”在天真的读者面前被彻底揭去伪装的面皮。
此类荒唐的逻辑也不乏追随者,他们甚至企图使人类的天文学由托勒密直接蛙跳到哥白尼,而这一步蛙跳几乎有1500年的距离。先后担任国英国欧文学院与曼彻斯特大学历史系教授的汤玛斯·陶特(Thomas Frederick Tout,1855~1929年)说:“看到还有人相信,一个人能够从伯里克利或奥古斯都时代一步蛙跳到美第奇和路易十四时代,这实在令人痛心……从头开始固然好,但是我们根本不能随意在某个时候停下来,跳跃过数百年,然后重新开始。”
约翰·威廉·德雷珀(John William Draper,1811~1882年)在《欧洲知识发展史》一书中仗义执言说到:“欧洲文献故意系统性地抹杀穆斯林的科学成就,对此我不得不表示悲愤。但是我肯定,他们再也不会继续被隐瞒下去了。建立在宗教敌视与民族自负基础上的偏见永远都不会长久。”
贝特朗·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年)也在《西方哲学史》中批驳说:“对于我们来说,似乎只有西欧文明才是文明,这是狭隘的偏见。”
在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1884~1956年)的《科学史导引》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一些荣耀的名字足以让人们想起,在西方是没有同时代的人物能够与这些名字相匹敌的……加长由这些名字组成的豪华的名单也并不是困难的。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中世纪的科学没有什么进步,那么就把这些名字读给他听,他们所有人都是在一段不太长的时期内——西元750~1100年,取得辉煌成就的。”
让我们回味一下乔治·萨顿的一句话的含义吧——“一个自以为是和虚伪的哲学家不可能理解伊斯兰的智慧,同样也应受到谴责。”
希提写到:“征服了肥沃的新月地区、波斯和埃及的国土后,阿拉伯人不仅占有一些地理上的地区,而且占有全世界最古老的文明的发祥地。沙漠的居民成为那些古老文化的继承者,渊源于希腊-罗马时代、波斯时代、法老时代和亚述-巴比伦时代的那些历史悠久的传统,也由他们继承下来……这些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在他们所管辖的人民的合作和帮助之下,开始消化、采用和复制这些人民的文化和美学遗产……他们是征服者成为被征服者的俘虏的另一个例证。”作为人类文化遗产链条的重要一环,可见阿拉伯帝国的文明在包容性与多元性上堪称典范。他进一步写到:“在整个哈里发政府时代,叙利亚人,波斯人、埃及人等,作为新入教的穆斯林,或作为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他们自始至终举着教学和科研的火炬,走在最前列……从另一种意义来说,这种文化是肥沃的新月地区古代闪族文化逻辑的继续……”
约翰·威廉·德雷珀还对伊斯兰科学的宽容加以赞扬,他指出:“在哈里发时期,学识渊博的基督徒与犹太教徒不仅受到应有的尊敬,而且被委以重任,提拔在政府中担任高级职务。”此类例子不胜枚举,例如“智慧宫”中的著名翻译家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Hunayn ibn Ishaq,西元809~873年,欧洲人称之为Joannitius,兼翻译家与数学家)就是一名基督徒。这种做法与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宗教裁判所疯狂毁灭科学,残酷迫害追求知识的学者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前文引用的文献作者皆为研究历史或科学史的著名学者。另外,也有一些“大众化”人物所言亦可稽考。但愿这些政治家或政客不是不学无术、胡说八道。
《自然辩证法》一书指出:“古代留传下欧几里德几何学和托勒密大阳系;阿拉伯留传下十进位制、代数学的发端、现代数字和炼金术;基督教的中世纪什么也没有留下。”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对科学史的评价。
美国前总统尼克森在《抓住时机》中说:“当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蒙昧状态的时候,伊斯兰文明正经历着它的黄金时代……几乎所有领域的关键性进展都是穆斯林取得的……当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把知识的边界往前开拓的时候,他们所以能眼光看到更远,是因为他们站在穆斯林巨人的肩膀上。”
七、结束语
世界上各种开放的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互相学习、互相吸收、互相补充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规律。
阿拉伯帝国的科学成就,其实是包括阿拉伯人在内的穆斯林共同体(还应包括帝国境内的非穆斯林),在吸收其它先进文化基础上的智慧的结晶。所谓的阿拉伯科学的主体,并非仅指阿拉伯人,甚至可以说当时多半著名的科学家与学者是非阿拉伯裔的。但是,他们以同一种的语言——阿拉伯语,书写科学著作。除了自身的探索之外,许多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甚至中国的科学典籍都是他们灵感的源泉。这些人类的文化积淀不但在他们手里被赋予一种全新的理解,而且他们自身也颇有创新,独树一帜。他们求知不倦,是“知识即使远在中国亦当往求之”的践行者。他们不仅是阿拉伯等穆斯林与非穆斯林民族的骄傲,而且其成就也是全人类的文化瑰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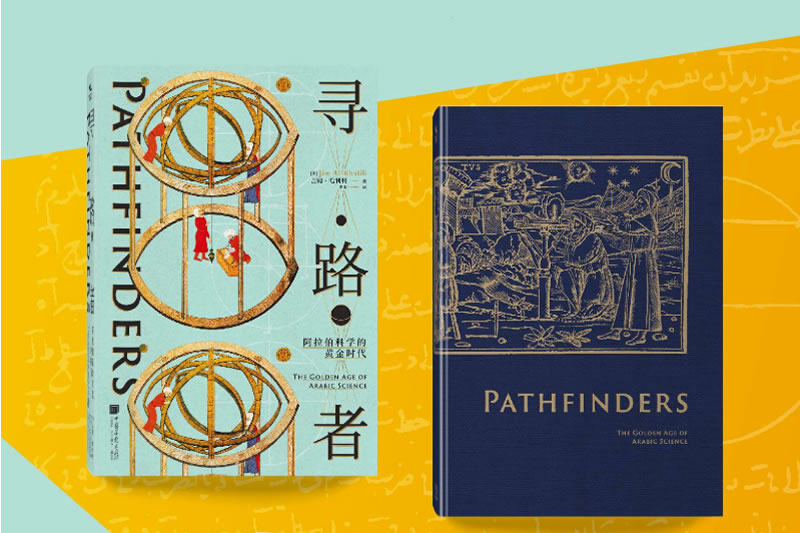

1条评论